在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接壤的草原上,有一棵饱经风霜的落叶松,卓然独立于茫茫旷野中,远处望去,参天古松,直插云霄。这就是闻名暇迹的"一棵松"。它不但是建立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活样本",也目睹了塞罕坝由森林到荒漠又到森林的生态演变,被塞罕坝人赞誉为"功勋树"。
历史上的塞罕坝,森林茂密,水草肥美,鸟兽繁多,辽金时期记载曾是"千里松林"的一部分。清圣祖玄烨于康熙二十年在木兰围场建立了"肄武狞猎绥藩"的皇家猎苑,塞罕坝是清王朝皇家猎苑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随着圆明园、避暑山庄等皇家浩大工程的兴建,"千里松林"被砍伐殆尽,清末国力衰退,后又招募垦荒,采伐不断,加之解放前屡遭山火,到新中国成立,森林茂密的塞罕坝已经破坏成"风沙遮天日"的一片荒原。
解放初期,频频袭击首都的沙尘暴,成了新中国的心患,也引起了林业部门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1957年11月,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承德专署建立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1958年11月完成了房屋土建工程。塞罕坝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人难以生存,再加上林场两年来造林成活率几乎为零,林场便主动要求下马。
1961年,林业部得知消息后决定派员考察,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的刘琨临危受命,带领陈希诚等6名专家前往河北塞罕坝实地考察。10月末的塞罕坝,寒风吼叫,大雪横行,俨然一派冬天景象。刘琨带领考察组骑马在人迹罕至的雪原上踏查了3天,终于在点将台的石崖下发现了天然落叶松的残根,又在红松洼一带发现了这棵粗壮挺拔的落叶松。这些珍贵的发现,为重大诀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塞罕坝机械林场不但不下马,反而要大干快上。一路上踏查的山川地理、历史凤貌、土壤气候等,都装在了刘辊的脑子里。他回京向林业部汇报后,便着手制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化林场的方案,方案中的四项任务之一就是:"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改变京津地带凤沙危害创造条件。"他心里非常清楚,要把塞罕坝恢复到昔日皇家猎苑的风貌,需要时间,更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坚守。
1962年,林业部建立直属塞罕坝机械林场(1969年归河北省管理),来自18个省市区、24所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和周边地区的千名职工,组成了369人的建设大军,迎着滚滚寒流,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吹响了"向荒山要树,还我森林"的战斗号角,拉开了塞罕坝艰苦创业的序幕。创业者们立志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职工没地方住,就住库房、牲畜棚,还没地住,就住窝棚、住马架子,有的从沼泽地挖草坯盖"干打垒"住,甚至随山就势挖地窨子住。一日三餐啃窝头、喝雪水、吃"苦力"、就咸菜。大雪封山,粮食供应不上,就嚼盐水煮莜麦粒。然而,林场两年机械造林成活率都不足8%,一时林场又刮起了"下马风"。1964年初,刘琨同志又上塞罕坝,他与林场技术人员一起分析失败的原因,根据塞罕坝的气候条件和土地条件进行了生产技术和机械改革。春季,林场进行轰轰烈烈的"马蹄坑大会战",机械造林一举成功,成活率达95%以上。这不但是塞罕坝机械造林的成功,也开创了国内使用机械栽植针叶树成功的先河。从此,"下马风"销声匿迹。此后,林场又进行大规模的人工造林。刘琨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林场的建设和发展,每隔三两年就到塞罕坝一趟,在视察指导工作的同时,看一看久经风霜洗礼的"一棵松”。
岁月的年轮记录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巨变,也记录了刘辊同志对中国林业的巨大贡献。
据《河北省志 林业志》记载:"1976年末,河北省的国营林场数量达到了160个,但在'文化大革命'前批准建立的林场,绝大部分未按建设期限完成建设(造林)任务。8个机械林场中只有省管理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按照设计进度完成了造林任务。该场在林业部和省直接管理的15年间,累计造林106.4万亩,年均完成造林7.1万亩。其他7个机械林场建场后累计造林1367万亩.......”
刘琨同志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林业改革和建设事业中。他日夜操劳,废寝忘食,为祖国的造林绿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也因此走上了国家林业部副部长(正部级)领导岗位。由于他的出色业绩和一身正气,被选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97年刘琨同志再上塞罕坝,是老部长从林业工作退下来离职休养期间第一次回塞罕坝。7月末,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接待了他,虽已年近耋耄,但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思维敏捷,谈吐清楚,声音洪亮。我和总场领导一同陪他特意看望了"一棵松"。那时,高大挺拔的落叶松约有20米高,笔直的干,笔直的枝。树干正好两个人合抱那么粗,在树干的7米多高处分出三条枝千,有两条向上又长成一条枝干,直插云宵,树梢上隐约有雷击的痕迹。树脚下用碗口大的石块堆砌围起来,可能是过往行人依树搭建的敖包,树底下敖包的周围是石块裸露的贫瘩土地。一棵古松在这里生长着,似乎要托起蓝天,岿然屹立,巍然远眺。刘琨同志默默地站在松树下,他与那饱经沧桑的大树对视,他的脸有些抽搐,是那么严肃、那么酸楚,又那么自豪、那么欣慰。人树相映,如同一对曾经.患难的朋友在回忆往事。那情那景,令我肃然起敬....许久,我们才告别了"一棵松"。
路上,他向我们简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原名叫林治安,1923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开始追求革命真理;抗日战争时期,为发展党的组织、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在孟良崮等不少的战役中荣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林业部门工作。然而在文革期间,建立塞罕坝机械林场竟然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听了刘琨同志的叙述,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到塞罕坝总要看看"一棵松"。这棵古松究竟生长了多少年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生长在我省纬度最高、气温最低、无霜期最短、土地条件较差的坝上高原这一端环境中是独一无二的。它忍受了孤独寂寞,经受了冰雪奇寒,经历了雷电劈里,抵挡了狂风暴雨......它仍然顽强的生长着,傲然屹立,气贯苍穹。它不单单是建立林场的活样本,更给人以精神的启迪。我明白了刘琨同志为什么要选择林业:选择了林业就是选择了清贫,选择了寂寞,就要忍得住孤独,受得住清苦,选择了林业就要以"一棵松"的坚韧、顽强、执着,牢牢地坚守在大漠荒原,深深地扎根在坝上高岗,奉献着自己的一抹绿色。
这人与树的经历竟是多么的相似!"一棵松",塞罕坝的功勋树!
他曾表表示以后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每隔两年到塞罕坝一趟。2000年,"河北林业艰苦创业教育基地"在塞罕坝建立的时候, 刘琨同志应邀参加了挂牌仪式。他虽满头银发但神采奕奕地站在主席台前,亲自揭牌并作了重要讲话。他的感情是深沉的,他的声音是铿锵的,他的语气是坚定的,他的期盼是久远的。期间他还挥毫书写了一幅赞美了今日塞罕坝的对联:"昔日塞罕风沙飞舞乱石滚,今日塞罕花海松涛人如潮"。2002年,也是塞罕坝机械林场建场40周年,他腿脚有些不便,但思维还是那么敏捷。虽不能亲自到塞罕坝,但还是深切关注塞罕坝,对林场的40年场庆提出了指导意见,对林场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2013年9月15,这一天值得所有塞罕坝人铭记!我们敬爱的老部长刘琨同志驾鹤西去。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按照他生前的遗嘱,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塞罕坝林场点将台下的苍翠林海中。老部长,您把魂留给了塞罕坝,您不就是深深扎根在塞罕坝上,伟岸挺拔的"一棵松"吗?
"一棵松",塞罕坝的功勋树!有了您,塞罕坝才有了百万亩林海,才有了"为首都阻沙源、为天津涵水源、为河北增资源、为当地拓财源"的绿色生态屏障。
老部长,塞罕坝的功勋树!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中,每当遇到困难、举步维艰的时候,您总是像"一棵松"一样,催人奋进。您已经融到塞罕坝的茫茫林海中,正昭示着塞罕坝的后来人!
"一棵松",塞罕坝的功勋树!你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力量之源,你是再造秀美山川的生命之魂,你是我们共建生态文明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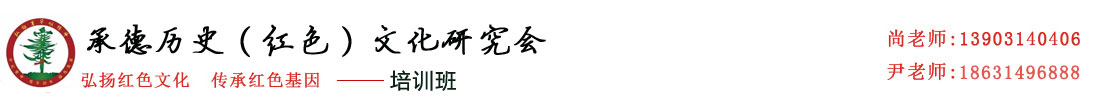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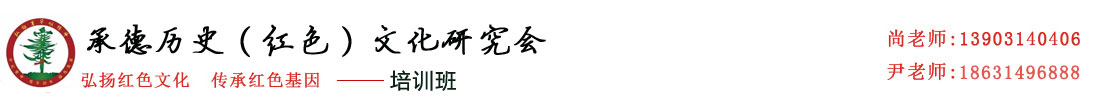
 塞罕坝精神
塞罕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