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岁月沧桑。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自1962年建场以来,经过了风风雨雨,走过了55年的历程。2017年她被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授予“生态文明建设范例”荣誉称号,被国家环保部授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文明单位”,获得了联合国环境署“地球卫士—激励与行动奖”。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事迹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总书记作了重要批示。荣誉的背后,是血汗、是牺牲、是50多年的坚守。当我们看到这一项又一项来之不易的荣誉的时,塞罕坝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第一任总场场长刘文仕。
刘文仕,1927年出生,这位20岁参加革命的丰宁人,曾在凤山镇任过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23岁任共青团丰宁县委书记,28岁任共青团承德地委书记,30刚出头就走上了承德地区行署林业局局长的岗位。他宽肩膀,高身材,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再加上说话大嗓门,干脆利索,典型一个豪放粗犷的北方人。1962年8月,刚刚建立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机械造林失败了,地委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兼任林场场长,于是他毅然辞去地区林业局长职务,说服了年迈的母亲,携妻带子,举家迁往塞罕坝。
在塞罕坝创业者的记忆里,场长刘文仕骑着一匹小红马驰骋的形象是永远也抹不掉的。他自上塞罕坝的那天起,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雪,无论是到分场检查次生林改造,还是检查农业生产,总是骑着那匹小红马。全场全部残存的天然次生林,造林地和农业生产所有的地块,都装在他心里;全场的大事小事他都要过问,哪里做的对,不管是谁立马批评纠正,有时不分场合真叫人下不来台。有的同志们不时私下议论:刘场长太不讲情面了,太严厉了!他典型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这个英俊而又充满朝气三十五六的年轻人骑上那匹小红马更显得英姿勃发。
刘文仕坦坦荡荡,光明磊落,胸怀全局的品格是大家所公认的。1963年机械造林失败后,林场人心惶惶,于是刮起了“下马风”。这一年秋季,刘文仕准备在上山踏查,主要是选地块,为“马蹄坑会战”做准备。踏查前他又翻看着机械造林成活率的报表,成活率不到30%,他胸中又升腾起不可名状的怒气。这时一个中层干部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递给他一封信和一份调动申请。他想刚开完会没几天,还有要求调走的?他打开信看着看着,怒火难以抑制,还没看完就连信带调动申请撕了个粉碎,扯着大嗓门气愤地喊:“你就准备等着埋在坝上吧!想跑?没门!”说完走出办公室,叫上随行的技术人员,翻身跃上小红马,一抖缰绳,疾驰而去。原来那封信是那位申请调动的干部托刘文仕朋友写给他说情的。那位干部呆呆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冒出一句:“真不近人情!”
刘文仕带领技术人员迎着深秋的寒风行进在茫茫荒原上,一会儿奔向山冈看地势,一会儿下马折一根灌木,在雪中扒拉出一块土地看看土层。当他看到刘琨1961年考察塞罕坝时发现的那棵傲然挺立的落叶松时,倔强地说了一句:“能长这么高的松树,我不信机械造落叶松就不活!”他仔细地端详这棵在茫茫雪原上独一无二的松树,浮想联翩:这棵高大的松树,笔直的干在向上斜生的树枝的簇拥下,多像一座塔啊!这不就是集体的力量吗?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也是任何困难都可以战胜的……他想着想着,仿佛又看到了上坝前他临危受命时林业部和地委领导们的目光,他又看到了国家林业部国有林场管理局刘琨副局长一次次来塞罕坝那坚毅的身影……他眼前白茫茫的雪野中出现了点点新绿,那点点新绿忽然长成了棵棵大树,棵棵大树汇集成绿色的海洋……
他们向宿营地北曼甸分场返回时,天近黄昏,又刮起了大风。当他们骑马走到石庙子附近的敖包时,山风卷着积雪嗷嗷地叫了起来。刘文仕知道这样的鬼天气,路不熟的人会迷路的。他使劲地一勒缰绳,蹬紧马镫冲向了前面,命令技术人员:“我在前面领路,你押后!”接着又大声地嚷着:“都趴在马背上!一个跟一个走,不要掉队!”他们回到北曼甸分场住宿时已是深夜了。他们跑遍了全场的山山岭岭,选中了一块名叫“马蹄坑”的宜林地,这块地三面环山,中间是开阔地,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马蹄,故而得名。那里既开阔平坦,土壤肥沃,地下很少有石头,距离总场不到10公里),应当最适宜机械造林。它南边还有一条潺潺的小河,水源也不成问题,而且又在前两年机耕过,是去年的休闲地。实验地块的选择为机械造林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刘文仕性格豪放爽快,为人直言快语,有话总是说在当面。1965年的深秋,刘文仕还是马不停蹄地在全场人工造林地块巡回检查,路过东坝梁时他发现一块地不太顺眼,便跳下马来,蹲下身子用马鞭子量着树坑,接着又东一个西一个地量了几个树坑,他的脸色变了。他回身上马奔向整地的第三乡林场,正巧在路旁遇到了林场的副场长。他举起鞭子往身后一指,大声地说:“那块地必须重整,抓紧时间!”说完扬鞭策马,奔大唤起方向去了。那个林场副场长先还有些怨气,到地里一看服了:如果不重整恐怕要耽误秋季造林了!
在刘文仕被“夺权”的几年里,他想方设法地给那些中层干部写纸条,告诉他们一定要组织好生产。总场林业科原科长李方文在《塞罕坝林业建设的简要回顾》中写道:“我和贾宝珍、李彦秋、范林、梁臣等几位中层领导成立临时生产领导班子,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负责全场生产技术工作。按着刘文仕场长的工作思路,在近两年的工作中得到各分场(队)的技术人员、营林员和广大工人同志的支持,使林场1967年、1968年两年的各项生产没有受到损失。”
1973年春天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刘文仕被“解放”。六年的“锻炼”更加坚定了他的意志!这一年的 7月22-24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员大会召开,刘文仕当选为党委副书记,继任总场场长。
他又想起了那匹小红马,不过那匹小红马已经成了老马了。而他还是那样意气风发,精神抖擞,他没有老,他依然年轻!他的脾气也没改,还是大事小事都过问。逢年过节,他不管分场的书记、场长谁在哪儿,不管是不是吃饭时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就摇电话,查防火岗。有人说他责任心太强,也有人说他太过分。他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还是干我的。
生活艰苦朴素关心职工生活是刘文仕的又一美德。大家都知道,刘文仕从来就不讲究吃穿,无论是在总场还是下营林区,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有什么地方住什么地方有时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从心眼里愿意和职工打成一片,从不搞特殊化。
1974年的冬天,雪出奇的少,防火一线的了望员在望火楼里度过了除夕之夜。1975年春节期间,刘文仕担心防火工作有人麻痹,也忘不下那些还在望火楼里值班的工人们。这次上山不骑马了,坐吉普车吧!他叫上司机穆士荣转遍了全场所有的望火楼和检查站。矗立在海拔1940米大光顶子山上的望火楼,是全场海拔最高的望火楼,它的了望面积最广。刘文仕知道这里的望火员又兼着护林员,春秋吃雪水,夏天吃水要到七八里以外的山下去挑,是全场生活条件最艰苦的望火楼。他把儿女孝敬自己的酒带来了,看到岁月的年轮刻在额头上的望火员老陈,笑呵呵地说:“老陈,你辛苦了!我代表总场党委班子给你拜年了!”说完把两瓶酒递到了老陈手中。老陈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临走时望着老陈深情地说:“这酒只为暖身子,可不能多喝误事!”……
1975年,老书记王尚海因为身体原因,调离塞罕坝,任承德地区气象局局长。刘文仕任总场党委书记、场长。
1977年10月下旬,刘文仕正在北曼甸林场蹲点整顿工作。10月25日这一天,塞罕坝普降瑞雪,气温在摄氏零度左右,26日和27日白天,天气阴沉,雨雪飘飘。到了27日晚上,地面的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那纷纷扬扬的雨雪洒落在树冠上,整个树冠的迎风面凝结成一层冰,雨雪加大,冰层加厚。每一棵树都挂满了冰凌,整个塞罕坝一下子仿佛进入了水晶宫:塞罕坝出现了奇特的雨凇现象。随着树枝上冰坨的加厚,树木承受不了重重的冰挂,开始弯腰断折。树木频频断裂的响声沿着山川传出几十里,那声响好像枪炮隆隆的激烈战场,人们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声音,都默默地流下了热泪。场长刘文仕是有名的硬汉子,“文革”十年的批斗和挨打没使他掉过一滴泪,看到这样的情景,他泪流满面。
他十万火急地乘吉普车返回总场,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北曼甸分场十几万亩天然林和人工林凡是椽材以下的幼树,全部被冰挂压断或压倒在地,椽材以上的甚至胸径几十厘米的大树,几乎全部压弯,有的拦腰折断有的树冠全部劈落。于是,总场几名主要领导,带领一些技术人员分乘几辆吉普车到东部几个分场察看灾情。刚离开总场十多里,几十里外树木的断裂声就盖过汽车的马达声,简直分不出个数,闹不清从哪个方向传来的……
总场领导分头连夜调查灾情,返回总场一碰情况,受灾面积和灾情程度远比人们估计大得多。全场东半部三个分场近四十万亩森林受灾,全场职工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人们放声痛哭。根据当时总场气象站工作人员统计和称量:一个五六十厘米长只有四五个分枝的小树杈,挂冰重量达到十公斤。二十多厘米长的一截草棍,挂冰重量达到一公斤,一株中龄树挂冰重量超过一吨重。 据《塞罕坝林场场志》记载:人工林受害37万亩,天然次生林20.2万亩;损坏中断电话线路260公里,折断木制电柱、水泥电柱666根。据抽样测算,树高3米,10年生的落叶松每株挂冰250公斤。”
刘文仕和全场广大干部职工没有被雨凇吓倒,他们擦干眼泪沉着应对灾害。总场及时向国家林业部和河北省林业局报告灾情,党委及时召开了会议,组建了以曹广德任主任,宋志和任副主任的救灾指挥部,购进器械12台,其中油锯4台。经过省林业局批准:总场严格按照经营程序及时组织全场进行清理,对受灾重、折干比重大、无保留价值的林分一律采取皆伐(把树木全部伐掉),对有保留价值的林分采取抚育伐,伐掉折干、折冠、掘根的树木,在不致形成“天窗”(林子里的空地)的前提下,伐掉被压木、病腐木,作业时尽量保护幼树……受灾林分的清理两年内结束。对皆伐的地块重新整地继续造林;对已经形成抚育后形成的“天窗”及时进行补“窗”重造。
面对自然灾害,塞罕坝除了从容应对。还有更多的思考:
同样挨着的两块林分,经营抚育方法的不同,受灾的程度也不同。于是刘文仕组织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进行营林研究。林场以后的营林中,改变了传统“隔行去行,隔株去株”的抚育间伐模式,一律采用了“去小留大,去弯留直”的间伐模式,使营林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78年底,刘文仕要离开他日日夜夜奋战了16年的塞罕坝,将赴三北防护林建设局任副局长。林业部领导希望他能把塞罕坝机械林场的绿化经验带到三北防护林的建设中。
上任前夕,总场开了欢送会后他要在塞罕坝走一走。他到了东坝梁,又登上点将台,在两处林场的高点,举目远望,集中连片的松林尽收眼底。这曾经浸透过汗水的森林呀,好像和他招手一一作别,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就是一匹马,在塞罕坝广阔无垠的原野上驰骋着,在岁月的风霜中他已经变成了老马,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据创业前辈介绍:刘文仕场长从塞罕坝搬家银川的时候,来塞罕坝时的家具是什么,搬走的候还是什么。这是一位多么廉洁奉公的党的领导干部呀!
人们不会忘记,他对一线普通职工的悉心关怀;人们不会忘记,他雷厉风行的工作风;人们不会忘记,他正义凛然的伟岸形象;人们不会忘记,他在塞罕坝不知疲倦的身影;人们更不会忘记,他带领干部职工在应对自然灾害中所表现的沉着。他离开了塞罕坝,带走的是塞罕坝的造林经验和工作作风,留下的是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的伟大精神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绿色情怀。他的身影犹如塞罕坝的绿色山峦和清澈的溪水,激励着每一个塞罕坝人。
刘文仕场长,塞罕坝不会忘记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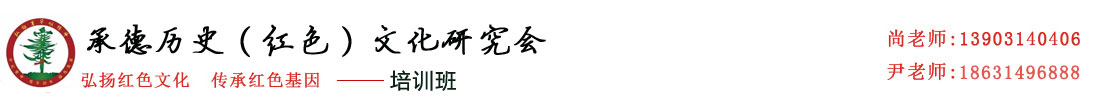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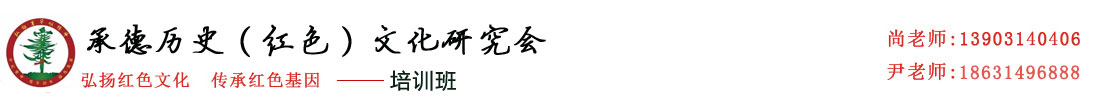
 塞罕坝精神
塞罕坝精神